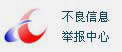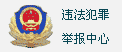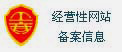○劉琴琴
王幅明老師的散文詩《汕尾紅,汕尾藍》以精煉筆觸和深邃意境,將汕尾地域的精神譜系鋪展于紅藍雙色的象征經緯之上。作者于“汕尾紅”里織入革命先輩的熾熱靈魂,“汕尾藍”中融入當代建設者的深沉智慧,更以三位汕尾兒女的生命故事為緯線,在時空的交錯中進行充滿詩意與力量的英雄敘述。
“紅”與“藍”在文中并非靜止的二元對立,而是構成了一種充滿張力的象征體系。“紅”是歷史深處那永不褪色的革命基因。作者對紅宮與紅場進行詩化描摹——紅宮墻壁的“裂痕”深藏震撼人心的故事,陳列的文物“沉默不語”,卻又仿佛在吶喊。紅場則是“天底下最美麗的廣場”,招展的紅旗,激昂的口號聲,先輩們堅定的足跡,讓汕尾成為一代代后人接受精神洗禮的圣地。而“藍”則是“大自然的賜予”“當代汕尾人的杰作”,這抹藍不僅指向湛藍清澈的海灣,更指向風電產業、海洋牧場等蓬勃發展的藍色經濟圖景。紅與藍彼此詮釋,相互護衛——歷史基因的“紅”為今日生態與經濟之“藍”注入不竭的精神動力;而“藍”的生機與壯美,恰是對“紅”所象征的理想與犧牲最富生命力的當代承繼。
作者更以三位汕尾兒女為載體,將宏大的歷史精神具象化于個體生命的壯麗詩篇中。彭湃作為背景式的精神坐標,其雕像在紅場成為永恒的精神燈塔。核潛艇之父黃旭華院士隱入深海三十年,名字成為“一串無聲的密碼”。母親縫補的棉衣裹不住北方的狂雪,父親臨終“望向北方”,二哥的葬禮“只有海風悼詞”——親人無盡的牽掛與犧牲,襯托出“對國家的忠,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”這一信念的動人心魄。深潛三百米的驚心動魄,“鋼鐵的關節咯咯作響”,浮出水面時“白發已與浪沫同色”,寥寥數語,勾勒出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科學赤誠。丘東平烈士的生命則如流星般短暫而璀璨:十八歲投身起義,三十一歲為掩護師生血灑疆場。作者巧妙聚焦其未完成的《茅山下》手稿,“被硝煙洇成泛黃的褶皺”,這褶皺是生命驟然中斷的遺憾,更成為永恒精神的物質載體。他“勇敢掀翻了日寇的鋼盔與刺刀,卻讓三十八個年輕的生命,在斷弦的小提琴上重新站起”,這充滿詩意的悖論,將戰士的犧牲與作家的精神重生完美融合。
在散文詩自由的天地中,作者打破時空線性桎梏,將歷史烽煙、建設偉業與個體生命熔鑄于一爐。彭湃、黃旭華、丘東平,他們分屬不同時代,肩負不同使命,卻共同構成“汕尾紅”與“汕尾藍”這宏大精神經緯中最耀眼的坐標。在“紅”與“藍”交織的象征光譜下,散文詩超越了單純的地域贊歌,成為一部關于信仰、犧牲與創造的深刻敘事。
王幅明在紅藍雙色的交響中,完成了對汕尾精神譜系的一次深情抒寫。他不僅鉤沉歷史,更讓歷史通過黃旭華、丘東平這些英雄的血肉之軀在當下獲得了嶄新的意蘊。紅宮斑駁的裂痕與核潛艇深潛的刻度,最終匯成了同一種生命意義——它證明地方精神譜系的書寫,正是以英雄的生命為墨,在時代卷軸上寫就的永恒詩行。






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
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