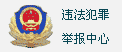○雪漪
逢甘霖、遇故知、花燭夜、題名時,舊版四大幸事。
新版未知,不好通過云計算羅列了。
說金榜題名時,在太陽升起的地方說,顯得更光芒四射。
麒麟子在天上,地位與龍差不多。狀元郎在人間,一抽象,后來比唐朝地位高。
那得意的春風,急速的馬蹄,催得我險些把史上狀元及第的佳話寫到抑郁。
學而優則仕的路,鋪出去一條又一條。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,帶我回到宋代。四十萬選一,儒生所求。
挑個日子,從白發回到他們青春的源頭。
院試、鄉試、會試、殿試一系列屢試不爽,縱橫交錯,走迷宮。論語、大學、中庸、孟子,召集在一起。要有問必知,頭頭是道兒。
誰知道,不識字的春風會翻到哪一頁停住。
廟堂之上,風吹過不諳世事。兼濟天下,天下熙熙攘攘,還有蜚短流長,掛著楊柳依依。
在張孝祥氣概凌云的水調歌頭中憶當年,收復中原脫口而出,三十八歲英年早殤,剩下激情勃發的忌日,定格于風雨飄搖。
楚莊王飲馬黃河,問鼎中原。不一樣的中原,不一樣的天。天地通道,中間隔著歷朝歷代,來來回回走著。
陳亮內心種植著愛國精神,在催得梅花一朵忽先發的地方抗金。這精神自帶光芒,月光似的奔走相告。
試試郭子儀武將的穆穆玄風,成功逆襲,挑唆今夜霓虹,各自為政。
大地蒼茫,沉浮誰主,才沒有民不聊生?
暮色向晚,我的眼里含著深沉憂患,不知置放在哪里,才能打開另外一條路。
此時,我人在天涯,與宋朝對坐,想寫一封家書。
四顧,后漢書替我提到無寄。
狀元味兒的江流與山色,開啟文人之畫,自王右丞始。一句話命中,文人畫登場,到現在不依不饒。
我端詳著自己的畫作,心有余悸。
折一枝張九齡的欣欣蘭桂,將開元盛世之美插在開元年間花瓶中欣賞一下,呈現給偉大時間看。時間若有所思,卻不言不語。
開元與盛世走在一起,可不是小事一樁。時隔多年,又在這里與我重逢。
閑云問野鶴,能責怪誰呢?
大路通天際,賈至革職之后多么瀟灑,偏偏喜歡與高適交游,與李白酬唱。
清歡在左,浮世在右,我必須借助一杯清茶,贊美這種生活態度。
執古之道,以御今之有,我的笑不能傾城。道德經下,很難書寫敬畏之心、悲憫之情。
這些走過獨木橋的狀元啊,曾經一定是挑開夜色,聞雞起舞之人。
月光已帶走初心,萬物歸于安寧。 文天祥欲填海的壯心,憂天的苦膽,托付給民族氣節,一一豈能都付楊慎笑談中吧。
大紅袍的故事,飄出怯怯蘭花香,在替誰感傷。
從昨日到明朝,著紅袍,帽插宮花。
從無人問,到天下知,熙來攘往的功名利祿,能忍的都忍了,不能忍的也都隨著皇榜壽終正寢。
我是對生活充滿敬畏之人,不敢向之討要更多。
你要為生民立命,你是武夷山為往盛、為萬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在一杯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茶中,我不用考慮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只考慮,無論歲月怎么更新,我要自己的定風波。
峰巒疊嶂,煙雨縱橫于大地溫床,曾是提供狀元及第的考場。
若尋一方山水,為靈魂閉關,就選茶樹王國武夷山吧。
朝曦迎客,晚雨留人,那是我靈魂的廣域。
作別大山十年,差不多忘記了你容顏。可否參股你的鐘靈毓秀,分一杯山泉,滋養我妙筆生花。
再贈一身霞帔,替我把身后功名拿下,挪到文字里穩定一下情緒。
在那里,我有不用考狀元的理想,可以擦干眼淚,唱水調歌頭。
“仙人”留下的一抹茗香,還掛在樹上,可以看見對面的朝暉與夕陽。
你的壯碩,節節深邃,挺出遠古的姿勢。大紅袍加身,多了一些陰影,一紙契約似的晃動。
若我路過,可以納涼。
一個歌者,要克服對武夷山沉默。多做一些與日月同輝的事,多說一些可以水落石出的話。
最后出場,蛇一樣脫胎換骨。
西風壓東風,不壓你的光芒萬丈。
一路所見所聞,整片森林里住著鐵羅漢、白雞冠、水金龜之名流。
你生死相依的弟兄,建設性陪在你身邊,行為意識里的手足視野,被大山圍著。
我喜歡一說到兄弟,就可以肝膽相照,就有兩肋插刀的人為天地立心。擺出秤砣的合適位置,為人間,說一句公道話。
這些對我來說,都不太強求了,尤寫你的時候,情感坐標定位只是你。
而我,是無以復加的一個載體。
四野碧綠,我是來客,看不到荒城。
泰戈爾想要外出的靈魂,來到我手邊,寫進來吧。
還有,敲著我心的門,想要進來的世界的靈魂。靈魂與靈魂相遇,需要識別。
朝圣路上,我聽說了永樂禪寺護佑著的蘭花魂。
你身上的名牌,叫得出口的大紅袍,不知道還有多少重量有所建樹。
套用高蹈這個語詞使用一下,國寶,高于自己的角色。
你的富與貴,你的稀世之珍,握著黃金毫不知情的手。
初心若雪的話,先對著雪說。彈響后漢書里的陽春之曲,再對著你說,和者必寡。
我用舊的昨天擦拭今天,溫暖純良,嘴角上揚,小范圍活著,剛剛好。
寫茶,是我賦予藝術的另外一個信仰。我希望,給茶寫情詩,與玉帛糾纏不清的,再也動不起干戈。
也許,一棵樹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名聞天下,只是需要樹站出來,給人能多看幾眼。
此際,與狀元無關,與我有關。
你閱歷太深,縱是詩意豐沛,你的高度不好企及。
一筆帶不過你的火紅歲月,就再來一筆。還不夠,就點上日出描一筆,再蘸上夕輝繪一筆。
更多時候,我沒有時間看日出,也沒有時間看夕陽。
有時,看殘陽,聲嘶力竭,喋血歌唱;有時,看殘陽,風靡如畫,醉上城樓。
大紅袍的紅,有特殊意義,有特殊的浪漫主義。
年齡、心情都穿一身鎧甲,可以一紙空文,輪流買單你的富與貴。
石骨嶙峋,站在路邊,默默無語。苔蘚,說著凡夫俗子的語言。
久違的一次拜謁,觸摸一下,尋根的文化名片。
作為一位曾經赴武夷山的拾荒者,身邊,一摞一摞歲月加高了各個狀元的舊夢。如今,到哪里也找尋不到我們的山河故人。
歸雁過處,無恙山河展示給你看。鄉愁,算是一處。
有恙的太多,不好挑出來說了。
一棵一棵,業已林立。盛名之下,其實難副。
從渴意、到渴飲,總結巖韻風骨的歸屬感,還真是有點難度。
萬千詩篇,抵押給你。腳步跟上了,靈魂卻扶搖直上。
我說,與大紅袍順利相遇,此大紅袍非彼大紅袍。
我舌尖的軟,沾著文氣清氛,仍然抿著科舉的前生、狀元的后世,吐出了思想的空氣。
我的臉上多了一種顏色:赧顏。
拽著大紅袍一角,好累好累。
一個人寫茶的時候,我選擇,不茍言笑。
你像你,像得太高貴了,做不了我的信徒。
挑肉桂二兩,才好離開武夷山。
想來的,不早不晚,已在路上了,天也給出了雪的答案。
清露下,滿襟雪,以謙卑之心問一句,能飲一杯無?
一江春水向東流去,那么,有誰可以傾蓋如故呢。
如果有,請不要做我的牧師。做我的船長,帶我出海,鴻鵠一樣張開羽翼。傳說,鴻鵠是那白色的鳳凰,許是夢里報考過我前世的狀元郎。
靈魂遠舉,我一出生就是冬天,偏就愛這一貧如洗的白色。
你看,這一生,出什么錯,都可以被你翻案。
【名家簡介】雪漪,一級作家,正高職稱,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。出版著作《靈魂交響》《我的心對你說》《只有遠方》《春天的合唱》,其中《我的心對你說》獲“中國當代優秀散文詩作品集”獎。






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
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