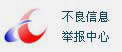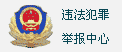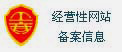○林煜琮
一路走來,有些喜歡會一直留在心里。對我來說,擺弄盆景、養花種草就是這樣的存在。這些花草帶給我最簡單的快樂,也寄托著我的憧憬,漸漸成了生活里離不開的一部分。
猶記得少年時與盆景初次邂逅的那個午后,在陸豐新華書店內,《嶺南盆景》的彩頁在陽光反射下泛著柔和的光澤。書中那些定格于方寸之間的山水意境——虬枝遒勁的古松、嶙峋奇崛的瘦石等,被稱為“立體的畫,無聲的詩”。盆景所蘊含的藝術之美,每一處細節都如同一把精巧的鑰匙,輕輕敲打著我的心門,讓我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。當指尖劃過書頁的剎那,仿佛有穿越千年的古老召喚,在二十歲的胸膛里點燃了一簇永不熄滅的火焰。自此,與盆景的緣分悄然生根發芽。
初次嘗試制作盆景的情景,至今記憶猶新。那時,我在陸城人民路建材店徘徊良久,最終咬緊牙狠下心,用半個月的生活費換回十幾塊大小不一的英石。灰黑色的石體上,蜿蜒的雪色紋路恰似冬日里凍結的溪流,充滿了詩意與想象。另外,我精心篩揀出潔凈圓潤的白石子,按照精確的比例將其與水泥調配好,再將小鋼筋與纖細堅韌的鐵線交織固定,憑借著十足的耐心,搭建起穩固的結構。完成后,我并未急于求成,而是靜靜等待了兩三天,待水泥完全干透,才手持工具,開始細致打磨。粗糙的邊緣在打磨下逐漸變得光滑,凹凸之處也被一一撫平,經過一番努力,一個獨一無二的花盆終于誕生。當夕陽將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,空氣中彌漫著水泥未干的氣息與汗水的咸澀,這一刻,成為了記憶中最鮮活的青春印記。
在盆景創作過程中,我總是全神貫注,腦海中不斷構思英石的最佳造型,反復斟酌每一處細節,再小心翼翼地用水泥進行銜接。盆景制作工序繁雜且精細,不僅要挑選合適的山石,仔細洗刷修整,還要將水泥與細沙均勻拌漿。初步造型完成后,仍需為盆景添上人物、亭閣、小橋等精巧構件。制作時,水泥的潮濕氣息與英石的礦物氣息交織在一起,縈繞在身旁。最終,一幅生動的山水畫卷在眼前緩緩鋪陳開來。然而,追求完美的我,多年來始終覺得它的造型未能達到心中的理想境界,于是一次次地砸掉重塑。每一次返工,都是我對盆景藝術執著追求的有力見證。
隨著對盆景藝術的癡愛愈加深沉,我開始四處尋覓更優質的創作素材。在早晨時分,有時我會特意趕到河堤邊的樹樁臨時攤點,滿心期待能尋得喜歡的天然樹樁。
堤岸邊,擺滿了村民們從深山老林、荒野溪邊采挖來的樹樁。這些樹樁造型千奇百怪,形態各異。當樹樁剛從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車車架卸下來,便吸引了眾多盆景愛好者蜂擁而至。大家一邊細細打量、評頭論足,一邊眼疾手快地將相中的樹樁搶占,隨后便是接連不斷的討價還價聲。談妥價格后,買到心儀樹樁的人難掩喜悅,小心翼翼地將樹樁綁在自行車后座上,揚塵而去,心里盡是即將創作盆景佳作的期待。
那時囊中羞澀,那些造型優美、姿態高雅的成型樹樁,宛如靜默的藝術品,雖讓我駐足良久、不舍離去,卻終究無力購入。幾番猶豫后,我選了兩株價格稍低、初具形態的小樹樁,小心翼翼栽在山邊老屋旁。心里總犯嘀咕,怕父親責怪我亂花錢——先前他知道我擺弄山水盆景時,就黑著臉訓道:“凈搞這些不賺錢的玩意兒……”望著他那雙布滿老繭的手,我太明白父親賺錢的艱辛,一時窘迫得說不出話,只能默默低下頭,不敢辯駁。
買了這些在他看來“無用”的東西,我只得每日偷偷跑去照看,澆水、觀察,盼著它們能快快抽出新芽。可終究是經驗不足,或許也有養護上的疏忽,沒能留住這兩抹新綠。望著漸漸枯萎的枝干,心里頭滿是悵惘,空落落的。
這份遺憾反倒點燃了我心底的熱情。或許是日子久了,父親對我種花養草的事不再反對。我便轉而尋覓更易侍弄的花草,幾株生命力頑強的三角梅、姿態雅致的南天竹,就這樣被我請進了小院。父親有時會站在盆景旁靜靜看一會兒,雖依舊沒說什么,卻也不再像從前那般抵觸。
從松土施肥到修剪造型,在與花草的朝夕相伴里,我慢慢推開了園藝世界的門,自此踏上了這條滿溢生機的種植之路。
這些年,我的陽臺上逐漸增加許多品種。清晨,南天竹的復葉在晨露的折射下閃爍著虹彩;榕樹的氣根如老者的胡須般悠悠垂落;而蘭花這位“花中君子”,最是考驗人的耐心與心性。那天清晨,我驚喜地發現蕙蘭抽出了第一串花苞。沒過多久,墨蘭也悄然開花了。看著這些粉白的、紫褐色 的花瓣輕輕顫動,我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,滿心都是歡喜。等到花兒完全綻放,清晨的露珠掛在瓣尖,在陽光下閃閃發亮,就像給翠綠的枝葉戴上了晶瑩的珍珠,美得讓人挪不開眼。
每天和這些花草相處的時間,是我最放松的時候。修剪枝葉時,我能暫時忘掉工作里堆積的報表,不再為生活開銷發愁;看到新芽冒出來,心里就特別開心,這種簡單的快樂比什么都踏實。科學雜志說,一盆龜背竹能凈化10平方米的空氣。可對我來說,這些綠植更像心靈的凈化器——每當被生活瑣事攪得心煩意亂,只要看看它們舒展的葉片、蓬勃的綠意,內心就能慢慢平靜下來。由此我感悟到,它們凈化的,是我在塵世中日漸浮躁的心靈。
每年春節的盆景展,都是我喜歡的盛會。我常常早早前往,穿梭于一盆盆精美的山水、樹樁盆景之間,腳步不自覺地放緩,久久駐足觀賞。這些盆景都凝聚著創作者的心血與智慧,它們或展現大自然的多彩瑰麗,或描繪田園生活的寧靜祥和,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。在展覽現場,總能看到白發老者對著作品低聲品評。在如今這個指尖輕觸就能獲取海量圖像和信息的時代,我們依然需要親手觸摸土壤的溫度,需要見證生命以厘米為單位的生長奇跡。
當朋友指著我的山水盆景說:“你這石頭擺得有點倪瓚山水畫的味道。”那一刻我才驚覺,那些年少時無師自學而制作的技法,早已悄然融入指尖,滲透進每一處石縫苔痕之中。






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
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